
头图来源|被访者
高瓴是谁?
四年多没见黄仁立(化名),他募了美元基金,跟合伙人在海外置办了些赚钱的买卖,得暇还能在办公室鼓捣杯“特浓”,催我试试那层咕咕嘟嘟的浮沫,特棒,他说。当年清华毕业,跑去斯坦福读书又回国,回来落脚,北京肯定是首选,随便数数这座老城的好处,掰两遍手指头都算不过来,他在这儿有根基,有人脉,所以偶尔还能碰见跟大人物做生意的机会,比如跟张磊。
美名校生聚会,在京城一度不好弄,“老凑不起人来”,黄仁立说,后来学校之间不时合伙搞搞,“斯坦福跟芝加哥合一年,又跟耶鲁合一年,拼出六七十人来,才算是个圈子。”人际交往嘛,有圈子才高效,有年年末,耶鲁校友张磊把亮马桥边上的高档办公室贡献出来,做了顿冷餐聚会,黄仁立头回跟张磊碰面,对方告诉他“你的每一封邮件我都会看”,这令他感到满意,“张磊人很好啊,很谦和”。
名校教育,回国投资,这部分际遇、选择,黄仁立跟张磊很相似,乃至更多同行,大都是这样过来的,某个时期后,他们人生都是金色的。只是,张磊成为了塔尖上的那个人,这是他的特殊性。
在聚会的这层办公室里,张磊经营着一家叫做高瓴资本的投资公司,此人正在越来越大的数字范围内具有影响乃至权力;他手里掌握超过4000亿人民币等值的基金规模,考虑到随时可以实现的配资、杠杆,他的资本调度能力远不止于此;他的事业、触手不断展现出更辽阔的可能性,以至于很多同业已经无法断言他的能力边界;他投资的企业遍布全球,并在每一块大陆上都成为产业引领者;高瓴甚至被拿去与华尔街的顶尖投资基金相提并论,他本人也被视为跻身全球资本话语权金字塔主流层级的几位中国人之一——甚至他某些时刻的谦和,都成为值得夸赞的美德。
用黄仁立的话来说,张磊正是当代所谓中国奇迹的典型——用读书改变了命运,被时势造就成英雄。时势造就的当然不只张磊这个个体,他们所生活的整座北京城,都像一颗钻石般,被科技、经济浪潮刷洗出大量不同面向的、璀璨的切面。十年前,市场间商业模式的信息差在这里是宝藏,每个弄潮儿站在台上,都掌握了那种迷人的C2C(Copy to China)商业故事讲述技巧;十年后,人们在乐此不疲地寻找坐实“弯道超车”的口径,要讲出一个拿得出手的商业计划也越来越难,你要在技术能力、市场规模、潜在红利等多个维度去阐述参与欧洲、东南亚、南美甚至非洲市场的优越性,当然如果以上都不成立,至少也应当先声明你全球化的格局。
高瓴资本便是全球化这个经济趋势中的庞然大物与投资行业碰撞出的产物之一,从创办这家公司之初,张磊就决定把口袋里那张耶鲁抬头支票里的美金花在中国市场上,14年后,关于全球化的洞察与连接,仍然是高瓴资本不同于其他竞赛者的能力基底。一个例子是,在面对某位记者将腾讯纳入“高瓴被投企业”这个角色来提问时,张磊马上强调“我在马化腾身上学到的远大于他学我”,随后又简短、隐晦地补充说,“在投资京东、国际化等关键问题上,我们有讨论”。
关于高瓴和张磊,是一则将全球化交织进命运主线的“当代中国奇迹”故事。这也构建了一个扭曲的视觉场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高瓴都像是行驶在另外一条车道上的赛车,没有与大多数人产生真实的交集,你能感知到它的动力、速度甚至发动机声浪,却始终无法真切、系统、深入地理解它。
让我们先把问题摆在这儿,高瓴是谁?

制表:《中国企业家》
位于链条末端的用户讲不清楚。你一定对这种句式感到熟悉,“或许你没听过高瓴资本,但我相信你有QQ号;用过百度搜索;在京东上剁过手;骑过摩拜单车;用过蓝月亮的洗衣液;在去哪儿网上订过机票;家里的空调是美的或者是格力的……”看上去,你无时无刻不在与其实现某种连接,你享受着由他们缔造并驱动的现代生活。但事实是,十多年间,除了两次被意外卷入新闻,张磊与高瓴的名字并未做过任何被推送至大众视野的尝试。
投资人也讲不清楚。多数同行可能会发现,甚至在“定义高瓴”这种最基础的问题上,你都无法与人达成一致。从宣传的主力阵地来看,高瓴反复强调在京东、江小白等早期案例上的表现,但没人相信他们是在与VC做全面竞争;曾在国内知名PE供职多年的朋友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们与高瓴是同行;但是很快便有人反驳,称高瓴与本土PE毫无可比性,基金币种都不同,你应当以复星为参照;也有观点认为,高瓴没有背靠任何产业集团,从收购百丽等大型案例来看,它是一只非常优秀的Buyout(并购)基金;还有一个答案,一位高瓴人民币基金的LP很不解地回答我,“他手里大部分资产都是股票,当然是Hedge Fund(对冲基金)啊!”
甚至内部员工也对高瓴满是问号。在一家母基金供职的朋友徐思季(化名)告诉我,近两年他收到的关于高瓴最惊人的消息,就是其旗下的高济医疗“不计成本”地收购药房,消息则来自饭局上遇到的高济投后某业务板块的负责人,“能扫的都扫了一遍,比华润这些央企快很多”。张磊在2019年某企业内部做分享时提及过此事,口径与百丽类似——看好线下连锁生意。但这位高济内部人士仍然怀有疑问,收购这批药店的执行成本高得不可思议,有些店流水很低,几百倍PE买回来,靠提效、做利润去寻求财务回报难度很大,“这种手法毫无疑问是产业资本,可我们背后的产业LP是谁呢?”
或许由始至终,对“高瓴是谁”这种问题有一百分解答把握的,只有张磊一人而已。那位很坦诚的高瓴LP用“没问题”穿插了很多提问,我们姑且称其为“没问题先生”罢。
没问题先生对我说,去年高瓴资本一级市场业务合伙人洪婧离职,接受了高瓴一笔投资后创办高成资本,这没问题,很多人除了张磊叫不出高瓴其他合伙人名字,这也没问题,“高瓴的Insights基本都从张磊这里出来的,我们也只在乎张磊。”
假如投资行业口碑的塔尖上搭着一座天平,那么两端被公认的名字只能是红杉和高瓴,在漫长的采访周期里,也不断有人在谈话中以两者作比。但现实地说,尽管都是在不可能赢家通吃的投资领域,做到了令人咋舌的优势地位,但两者绝不类同。过去几十年,作为全球品牌的红杉资本,在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乃至合伙人机制上都证明了其传承能力和制度的有效性,而对于成立不过14年的本土机构高瓴资本来说,它绝大部分的可能性仍然紧紧系于张磊一人身上。
问题在于,多年来,张磊恪守着一个优质的投资人信息管理品德,所以你会发现,在时间流河的很多段落里,你检索不到此人的存在,他似乎也无意用贩卖经历的方式塑造自我:一位研究机构合伙人聂濂(化名)跟我说,尽管公开信息称高瓴成立于2005年,但在2010年投资京东之前,他对张磊此人没有任何印象。那么,这种信息错位反过来更加证明了事实的怪异:如果连“高瓴是谁”的问题都无人能充分解答,那么高瓴又是何成为“今天的高瓴”呢?
人们有时会错过某些原本可以成为时代注脚的名字,到后世才会扼腕。蛰伏在顶尖企业名声背后的张磊,多年来都是个模糊的、不为人真正通悉的标签,正像是那个在信息变革的盛世之初被看到,又被错过的人。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近一年来,高瓴和张磊对外输出的信息量明显增加,高瓴资本开通了官方公众号,举办了“瓴峰会”,张磊的言论也开始频繁出现在视频中、网站上、朋友圈里,他被动地获得了穿越“奇谈故事”的契机,正在来到当下。
某种意义上,张磊和高瓴是同个事物的一体两面。摄影上有个“魔幻时刻”的说法,意指黎明时分光线暧昧难辨的七八分钟时光,我决定抓住此人“来到当下”的时间窗口,在天色将明未明的魔幻时刻,去搜寻、整理人们手上的信息切片,拼贴一个高瓴。
老钱的纪律性

来源:被访者
关于那次高瓴办公室的聚会,除了感知到此人热心肠,黄仁立也意识到,校友社交显然对张磊也很有裨益。其实不仅是裨益,校友圈层正是张磊人际关系网里最重要的一条脉络,一位接近高瓴的朋友告诉我,当年张磊在耶鲁校园基金时期共事的同学、同事中,很多人如今在美国各大捐赠基金任职,构成了高瓴资本重要的美元基金LP基石。
这也是高瓴在产业资源上经常令人感到咋舌甚至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例如聂濂对张磊“搞定”美国梅奥诊所一事的态度,就显得意味深长,他对我说,双方合资在中国创办“惠每医疗”在业内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简直超出一般商业资源能力范围,梅奥在美国来说至少是协和这种级别,拿到这种跨境资源,确实厉害”。在这一点上,张磊在前述企业内部分享时,提到过与梅奥的关系,他的说法是,双方以投资的形式绑定在一起,梅奥旗下那只200亿美元规模的捐赠基金,正是高瓴资本的LP之一。
所以张磊早年向耶鲁捐款一事,也需要从两个层面去理解。黄仁立觉得,最大程度上成就了张磊的,毫无疑问是耶鲁,而不是他本科就读的、后来向其捐款更多的人大,抑或早期供职的五矿;此外,耶鲁校园基金时期师从大卫·史文森的工作经历,也奠定了其投资风格底蕴,“首先学经济的都有这种路径依赖”,更遑论耶鲁标签如今在资源与资本两端,都对高瓴形成了巨大支撑,双方绑定很深。
我的同事目睹过一个饶有意味的事情,某论坛Panel散场,人群涌到台前将张磊围起来,其时,某位一线投资机构负责消费的合伙人竟也手持名片,悻悻然挤了进去——人的江湖地位,就是这样被人捧出来的。那位接近高瓴的人士告诉我,作为当下最受传媒、企业家乃至投资同行追捧的人之一,他有充分的余地来选择与身边人事物的亲疏远近,不会放任所有贴近的标签都与自己形成深度绑定。
一位国有金融机构的投资人单恕(化名)觉得,高瓴对外的话语体系构建得非常好,“理念的构造对一家投资机构来说太重要了。对张磊这样级别的投资人来说,show up很重要,什么场合出现非常重要,对大家对你的理解更重要,投资本质上是个marketing的行业,你要搞定LP的同时也要搞定企业家”。
张磊不长于讲演,公开场合常表现得谦和;他习惯五指捏住话筒,像是掂量、拿捏着手里的话语权;他会在换气口主动发笑,对听众来说,满是善意;但别误会,即便在这些时刻,这名不以谈吐见长的投资人也从未放松过信息把控。几年前,张磊在香港参加一场规格颇高的金融论坛,同台的分别是从央行转赴银联担任董事长不久的葛华勇,以及时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这种场面下的对话,三位嘉宾必然会被分割为代表着“传统”与“创新”的两个阵营,主持人顺利地将谈话重心偏向被分配了第二类角色的张磊身上,而当被连续追问与梅奥诊所的合作细节时,张磊却开始谈论起高瓴与这家美国医疗机构在长期价值观上的一致性。
张磊与合作企业间的远近博弈非常有看点。投行人士唐军(化名)告诉我,张磊与很多顶尖企业的关系绑定紧密,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在相关项目上获得最早入局的机会。2013年,高瓴就牵头了与腾讯、印尼最大的媒体电视平台Global Mediacom在当地成立合资公司的案例;此外,包括爱奇艺和后来的京东物流,高瓴都因为基于和企业的良好关系具有先发优势,但唐军觉得,高瓴虽然很早也投资了百度,但关系并没有在台面上捆绑得很紧,“他很少提百度”。一位参与了京东物流首轮投资的投资人向《中国企业家》透露,其实最早参与京东物流独立融资谈判的机构不过四五家,而越是行情低迷,大企业分拆项目越是争得厉害,最终大大小小的资方“挤进去四十多家”,只是尽管如此,高瓴仍然当仁不让地联合红杉完成了领投。

来源:IC photo
谈论减持京东是另一个让高瓴LP“没问题先生”感到无趣的话题,他首先指出,高瓴被曝出减持京东和投资京东物流的时间点大致重合,因此印证了高瓴的投向往线下传统产业转向的大战略。此外,遵守纪律性地在商言商才是正道,“减持京东是因为京东增速放缓,买红黄蓝是因为红黄蓝便宜,这都没有问题啊!”
游弋在企业家当中,凭着市场规则做生意,这两条线索之间的博弈和拉扯,正是东西方投资文化在张磊身上的交锋。一位转行做VC的媒体前辈向我指出,在很多高瓴的生意上,你能看到美元基金那种典型的“老钱的纪律性”,这与国内很多人民币基金差异巨大,因为有不少国内的资本内心笃信:关系和钱搞定一切。
回过头来说,如果“没问题先生”是对的,那么,谈论高瓴减持京东的媒体,都是趣味乃至价值判断被扭曲了吗?我们来简化一下事件要素,高瓴始终宣称相信价值投资的意义,而投资京东这个案例,又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对此承担着解释职能,因此,当高瓴选择减持京东,就等于放弃这种解释口径,因此势必要求张磊对价值投资有个新的说法,抑或拿出新的标杆案例。黄仁立觉得百丽可能是那个新的答案,他对此事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如果说是京东和腾讯定义了高瓴最初十年,那么备受瞩目的百丽私有化,很可能将是高瓴未来再塑格局和高度的关键。
无论如何,京东对于高瓴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被投资企业或者合作伙伴。前述研究机构合伙人聂濂觉得,高瓴资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二级市场上游弋、铺垫,其中有些投资为他带来了财务回报,比如在洋河、青岛这些酒类股票上的抄底成功,有些则为其撬动了更多资源与合作,比如从设立之初,高瓴就投资了腾讯、格力、美的,除了与腾讯长期密切地联系之外,很多家电领域的企业家,也成为了高瓴的LP。只是,在二级市场之外,如果说张磊由哪一刻开始,真正拿到了互联网那张船票,那么一定是从投资京东开始的。
如今这家电商巨头仍然深陷多事深秋。“简直炸毛了”,参与了京东物流投资的人士说,尤其是刘强东那封发给配送员的内部信里“交了个底”,披露京东物流2018年全年亏损23亿,并回溯称是第12个年头亏损。这个行为,有没有帮助其本人解决内部舆情问题尚未可知,但显然是将出资的股东推进了更大的压力场内,“披露这些信息对投资人很不友善”,该人士说,“我们的LP也都会看到,所有京东系的公司都受影响,真是火烧眉毛。”
张磊自始至终未对京东的事情发表任何看法,只是最近接受财新的一次英文访问时,谈到了创始人和长期价值投资两个话题。
“中国企业向来是创始人驱动,这很好,但我们关心的是企业转型,我们担心创始人驱动的文化是否能建立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团队,帮助公司走向下一个阶段。”
“坚持长期价值投资,不代表你的投资策略一成不变。”
“亚洲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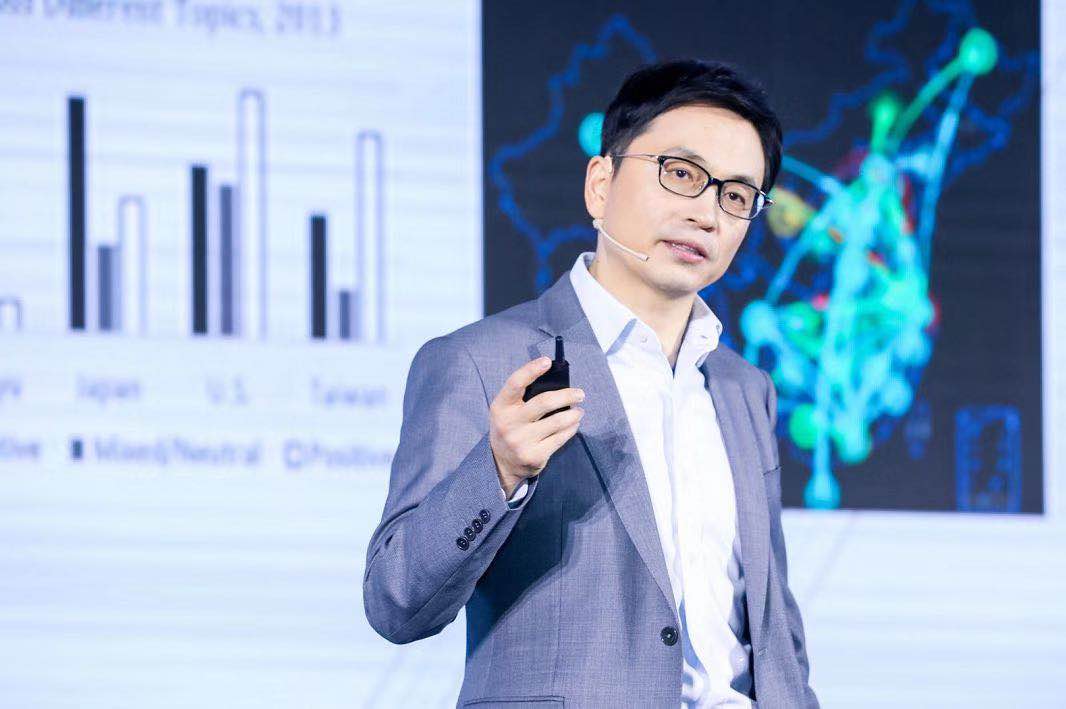
来源:被访者
高瓴与外界保持紧密同步的信息或许只有基金管理规模,并很早喊出了“亚洲最大投资基金之一”的口号。
风险投资行业的规则之一,是要在更早的时间点与最优秀的企业家建立关系,所以很多基金从策略上越来越倾向于在最早的投资阶段切入,但对高瓴来说,在早期投资的追求上却显得暧昧。首先从口径上,高瓴也会强调很早投资了江小白等案例,但同时,其一级市场上的投入的资本占比却委实很低,按照没问题先生的说法,“应该不到10%”;此外,在去年洪婧离职之后,高瓴的VC团队也重新组建,不到10人。一位投资同行说,高瓴在偏早期阶段的投资很积极,并且由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延伸出来的投资在行业研究上有其优势,但毕竟对他们还是个新领域,目前来看,很多项目投得价格不低,走向还得“再看看”。
那么对高瓴这样的机构来说,核心实力在于什么?在这其中,VC阶段投资的意义有多大?聂濂觉得,张磊作为基金管理人,首先考虑的一定是面向LP的价值,长期来讲,早期投资在高瓴这样的巨型基金里无法产生有效持续的回报数字,“VC那些资产,在IRR里影响的是小数点后边的数字,做得好与不好又能怎么样呢?”
在企业家一侧的影响力,聂濂认为也不能用“最早建立关系”的逻辑去审视高瓴,“最早建立关系”的价值,会被更大体量的基金规模和资源实力去覆盖掉。“我管着六百亿美金,你管着六亿人民币,你告诉我说你在企业家那边的分量比我高?开玩笑,肯定不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在资本市场上,大,往往意味着压倒性的优势。“早期关系这个逻辑,对红杉来说就是有效的,因为他们基金足够大,但对大多数早期投资机构来说,关系本身形不成长久的优势。”
过去很多年间,对于投资基金来说,小而美也是一种被承认有效的经营策略。但2018年发生的那件事,显得异乎寻常,起码,在多数人没有厘清认识之前,它被认为潜藏着改写创投行业规则的可能性。这件事就是孙正义为愿景基金(Vision Fund)募集了一只100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阿联酋Mubadala投资基金和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投入了共计600亿美元的资金额度。业内有消息称,这两只来自中东的资本原本询问过红杉资本的募资意向,但如此高额的资金规模当时并未被红杉接受,而当孙正义的基金推出后,全球的风险投资机构都被迫成倍地将基金规模提涨起来。启明创投创始合伙人邝子平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巨大变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不透”。国内一位人民币基金的合伙人对我说,起码在美元基金里,最近的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她的理由是,包括红杉、高瓴乃至GGV的美元基金全都超募了,而高瓴新美元基金募资额最高,最终被披露的数字是,106亿美元。
很难说高瓴这只再次喊出“亚洲最大”口号美元基金的募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孙正义的影响,但至少就张磊来说,他对“做大”是有着全面的、不可动摇的、长期可持续的信念和执行力。那位接近高瓴的人士告诉我,张磊在很多事情上会习惯性做出“搞大”的判断,当然,在对外谈论类似观点时,他会换一个表达方式,叫格局,这总会令他看上去气象昂扬,比如在收购了百丽之后,他告诉媒体说,高瓴从来没有想要通过削减成本去帮助这家零售巨擘提效,“我们反而提高了投入成本,这将是一个更大的生意”。事实上,在投资行业里大部分的商业判断中,“大”才是核心信息。
单恕告诉我,这个行业,钱不够多就上不了桌。“单笔投资能拍出三亿美金的核心投资人,在中国可能也就二十个,高瓴是其中一个。”
私募基金回报数据并不透明,高瓴是凭什么被公认为最好的那一个?当我对那位人民币基金合伙人提出这种问题时,她推敲了许久,给我的答案是“持续做大就是证据”——基金规模600亿美元;员工人数超过300;百丽单个案子规模超过500亿港币——从经营、管理再到投资都是被客观结果证实了的。
单恕也认为,外资市场上很多美元基金的榜单排名标准就是看AUM(资产管理规模),“美国人非常认这个,你规模如果是第一,业绩一定差不了”。
大的好处也显而易见。聂濂给我算了笔账,高瓴宣称的基金规模超过6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4000亿,对于这类最头部的机构来说,2%的管理费几乎没有折扣,即便考虑到一些基金存续的问题,实际算来,高瓴每年的管理费收入也至少在几十亿元人民币——这甚至是个超过很多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规模的数字,也为高瓴在很多方面带来了难以媲美的竞争空间。
“规模优势到了一定阶段,deal sourcing就会越来越好,这个行业拼的就是信息差、关系差和规模差,信息差现在越来越小了,规模差、关系差就是你的市场地位。”单恕说,“你能调动的资产规模和你的社会影响力,决定了你与他人的供需关系”。
在招聘市场上,高瓴也掌握着充分的话语权,一位关注投资行业多年的猎头告诉我,至少在标准化的薪资结构里,高瓴的offer是最高的一档。在她提供给我的一份去年的报价列表里,数字是“肉眼可见”的高,“他们招得起最顶级外资基金的人”。
但在用人标准方面,高瓴则是透着一种外人难以描摹的气质。有领先的薪资供给,那么其用人标准一定极为苛刻,例如,此前一位被挖走的人民币基金高管就没能在高瓴立足,不久后就有同业听到他再次去职的消息。但同时,那位猎头又告诉我,曾经先后有四位在某家一线机构处未通过面试的PE人才,被成功推荐入职了高瓴。“只能说标准和别人不太一样,起码那四位看上去都偏乖一点,像履历漂亮的好学生。”
我在采访最后阶段,拿到了一份高瓴人民币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说明书》)。《说明书》的信息显示,高瓴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原本由张磊与洪婧、易清清、李良、马翠芳五人组成,但在洪婧离开后,有消息称原董事总经理曹伟晋升为合伙人。而这些人在加入高瓴之前分别来自中金、华夏证券、华平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
这也印证了单恕的一个观点,起码从人才构成的背景上,高瓴并不是那种非常耀眼的团队,“你看博裕资本,马雪征、张子欣、童小幪,这都是在PE行业打过大仗的人,但高瓴的团队完全不一样”。前述人民币基金的合伙人也持类似观点,她觉得,高瓴的投资团队,没有那种超一线团队常见的“sharp”。同时,高瓴的投资团队在公开场合与媒体上曝光较少,除了从外部请来干嘉伟、苏敬轼这几位运营合伙人之外,官网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人员信息。在采访中我发现,外界甚至没多少人叫得上来除张磊以外的合伙人名字,他们像是被磨掉了的硬币反面,面目模糊。但这对高瓴来说,谈不上优劣,“因为他们的业务不太依赖单兵作战,只要张磊足够强,打群架赢了也是赢啊”。
为持续做大付出的代价也不是没有。黄仁立说,尽管市面上无法看到高瓴全面的业绩数字,但用投资行业惯用的回报倍数来衡量的话,你很难相信它的倍数有多顶尖。逻辑在于,要在“大”这条策略上走下去,强化某一侧的优势的话,就必须要做更大的案子,而这就面对另一个悖论,“基金越大,可投的项目越少,在必须完成的投资压力下,有些项目标准可能就没有那么顶尖了”。
从几年前开始,高瓴这艘巨轮就循着张磊在消费、医疗几个方向的思路来探寻航道。在科技互联网带来的红利被市场吞噬干净之前,张磊就在“能够与科技能力有效融合的传统行业”里连续重注去买下一张船票。
局内人

摄影:王攀
投资这行当对很多人来说,核心即是构建交易、匹配资源的买卖。黄仁立有几位年轻的朋友在国内几个大型PE供职,偶尔以个人名义投资些项目,因此断不了做些个FA(财务顾问)的活计。黄仁立发现,他们每次都会把项目推给高瓴,但从没获得过投资。“高瓴对项目确实很挑剔”。
挑剔只是一方面,或者说,挑剔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唐军看来,是高瓴“做局”的能力,是构建生意体系的能力在发挥作用。
没问题先生也清楚地向我指出过这一点的另一个表征,即“高瓴不重视growth阶段的投资”,这是个令人感到非常有趣的事情:作为投资人,策略上故意避开企业增速最快的那部分资产。没问题先生的说法是,市场在这类项目上抢得太凶,对高瓴意义不大,“想要回报倍数就押早期,想要回报数额就做二级市场,没问题,很清楚”。
张磊喜欢用一些又正确、又没信息量的方式做表达,比如“弱水三千但取一瓢”这种话。所谓信息含量低,原因在于这话适用于所有投资机构,每家投资公司都只能寻找一种恰当的生存逻辑。只是对高瓴来说,基于充分的自信,在执行上更加坚决,“growth投得少”就是一个例子,几年前,黄仁立的一个经历也对此有印证。他曾向高瓴推荐过一个医院的投资机会,按说这种资产,数据漂亮、壁垒高企,十拿九稳挣钱的买卖,可尽调后,高瓴却推掉了此事,给出的理由正是“太贵,其他人抢得太厉害”。
几年后,黄仁立遇到一位高瓴合伙人重提旧话,说后来投入此项目的3个多亿人民币3年就完成了退出,IRR达到19%,对方也只是笑笑,过去了,“我猜他言外之意是‘不过如此’嘛”。
西方金融市场里,一直有个“造雨人(rain maker)”的说法,多数用来赞美一些做出标杆案例的投资银行家,意指“没雨的时候能让天空下雨,在没有交易的地方能使交易发生”。黄仁立觉得,张磊的独特之处,就是他作为一个基金管理者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作为市场买方,又能够深度绑定一些企业家关系,构建出属于自己的交易和生态,“早年方风雷(厚朴基金董事长)就被尊称为造雨人,现在看,张磊完全也可以,并且格局更大。”
如果用这个逻辑来审视高瓴,那么“张磊造雨”的集大成之作当然是撮合腾讯投资京东。我们绕个小路,从一本书谈起,在美国作家纳博科夫一本名为《普宁》的小说里,写到一个8岁的孩子“画空气”的怪异故事,孩子的做法是,依次把苹果、铅笔、象棋、梳子等物件放在一杯水后面,通过杯子,红苹果变成一条轮廓鲜明的红带子,梳子平着放,玻璃杯里就充满了条纹,成了斑马香槟。
换句话说,当你无法明确一件潜藏事物的意义时,去审视“它的缺位”,或许是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对投资公司来说,钱与钱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你的存在意义,是否就存在于你“缺位”的那个假设当中?
黄仁立为我推敲了这个假设。2014年,腾讯、京东由张磊牵线达成战略合作之后,微信就为京东开放了一级入口,至今京东有1/4的新用户来自微信。而对腾讯来说,除了通过京东攫取到百亿规模的财务回报之外,更重要的是阻击阿里,并在几年后,在微信生态里等来了拼多多。此外腾讯联合京东投资唯品会,乃至今年再次以微信与京东深度合作,阿里携手苏宁等一系列变化,都由2014年的事件肇始。那么对于高瓴和张磊缺位的假设,这个答案就显而易见,至少电商这个令中国互联网全球领先的产业,会存在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对一家投资公司来说,被认为在经济产业某个局部某个时点“不可或缺”,简直是个至高层级的褒扬。

摄影:史小兵
巨人握手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深究的落点在张磊身上。互联网此前几年在快节奏地弥缝整合,有不少攫取巨额回报、撮合同业合并、结束局部争夺的人和事,会被长久地作为经典商业案例记录下来,而腾讯投资京东在两个维度上具备不可超越的特殊性,其一是体量,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单买卖都是电商最头部的公司角力。其二,即是张磊在其中介入的功能和价值,绝不止于一个撮合角色,反而是参与者。
这让我想起,去年饭局上从一位媒体前辈那儿听来的一番话,据他观察,市面上有三类人群长久地持有一种“局外人”心理,这天然需要在复杂关系当中谋生的人分别是:咨询师、记者以及投资人。
我偶尔碰到机会,拿这观点当佐料,跟一位头部基金的合伙人勾兑过话头,对方的反馈倒爽利得很,“没错”,他说。
“怎么是局外人呢?你们可有董事会席位。”
“那又怎么样?你即便投了美团,也顶多出出主意,带几万兵打仗的也是王兴。”
黄提醒我,同样都是构建交易,在腾讯投资京东的案例中,高瓴资本作为参与者的重要性非常独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高盛,在那本据说所有入职员工都被要求阅读的《高盛帝国》里,阐述过这家全球最具权势的投行的价值观:由资产管理(投资)挣得1美元的市场价值,是由交易收入(投行)所得1美元市场价值的4~5倍。“表面上是撮合交易,张磊的行为本质上是投后管理。”黄仁立说。
接下来,他用了一个更加奇诡的比对来向我阐释此事,这种投后管理在资本市场上实现的效率,简直堪比造假:上世纪90年代的A股里,曾有一批投机者在购买酒类企业的股票之后,同步在线下集中采购大批白酒,待股票价格因为销量提振起来,即可套现离场吃到溢价,而整个过程中,这批酒都在酒企仓库里,原封不动地存放着。而对高瓴来说,在投后管理的价值逻辑上也是如此,甚至不需要像投机客们似的在台面下动手,仅凭公开构建交易,即可实现高效的多赢,高瓴作为股东,赚取的是翻上去的市值,“但凡帮企业多做2000万利润,那边就有15倍市盈率等着呢,多估出来3个亿”。
这就是当所谓“全链条”“生态”“覆盖能力”能够真实落地的时候,你在生意里能够攫取的现实的、巨大的回报。黄仁立觉得,张磊最近几年越来越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多说话,少办事”。多说话我们先不表,在这里,“少办事”即指对投资绝对数量的控制,在其构建的生意之外出手次数降低,“董明珠的MBO也传高瓴在跟,因为他一直持股嘛,张磊肯定不会深度参与,这不是他的‘局’。”
说老实话,参与者也好,做局人也罢,采访再多人我心里也留着忖量,这原本就都是外围观点。但在拿到那份高瓴募资《说明书》后,里面关于投资流程与竞争优势的一段阐述令我哑然,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高瓴通过广泛交流,打造行业‘局内人’地位,灵活应用跨地域、跨行业、跨在线/线下的资源,融会贯通、独辟蹊径地形成独家的投资创意,主动发掘和储备适合本基金的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理念的潜在投资机会。”
重新定义高瓴

摄影:邓攀
那么,哪种投资案例才是“高瓴的局”?显然百丽是目前高瓴在人力、资金、时间成本最大的案子。而随着采访深入,一个问题愈发凸显出来:百丽私有化会像9年前投资京东一样,成为在更大格局上重新定义高瓴的经典案例吗?
《说明书》里有个关于投资理念的抽象说法,可以先摘录在此。
“高瓴恪守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理念,深谙全球行业规律,并能准确把握行业变革的要素和时点,聚焦具有长期持续的结构性竞争优势(护城河)、投资回报卓越的业务模式,谨慎而坚决地集中投资、长期持有。”
为了避免让抽象理念沦为正确的废话,就要求你能具象地描述它。前述研究机构的合伙人聂濂说,要理解高瓴今天的打法与核心竞争力,百丽无疑是个最好的通道,就目前来看,这是个有着强烈高瓴烙印的私有化案例,其间的独特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交易规模,百丽私有化估值最终落在531亿港币,高瓴在其中持股57.6%,也就是说,高瓴要独立出资300亿港币左右,对一家投资基金来说,这种在单一项目上投入数百亿港币的承载能力,在国内也就头部十余家基金具备。
此外是视野。从这个概念穿透去看,背后是高瓴为人公认的优秀的研究能力。聂濂告诉我,相对于有些机构怀抱着“财务投资,占小股,用技术能力提升零售效率”的认识,高瓴直接以私有化方式接入零售产业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对产业更深层次的理解。“如果他把百丽改成了‘卖鞋的盒马鲜生’,那么整个估值体系就全都变了,你能把百亿的项目翻十倍,比把十亿的项目翻百倍要强得多,你藉此获得的认可,对LP的影响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如果说前两个要素,尚不能构成高瓴的核心壁垒的话,那么在百丽这个案子的执行上,高瓴的做法,释放出了更多异于PE控股型收购的信息。其一是参与方,百丽的高层团队基本保留了原始结构并仍有持股,也就是说,虽然高瓴主导了此次收购,但借用的仍然是原始团队的产业能力。
没问题先生也向我分析说,此前春华资本和中信资本分别收购了肯德基与麦当劳,但绑定合作的是蚂蚁金服与中信股份,“可你看高瓴收购百丽的合作方是谁?鼎晖”。鼎晖在其中解决什么问题?他认为,鼎晖在退市和重新挂牌这层面的运作经验很好,但经营方向,高瓴一定是打算自己操盘了。
据接近高瓴的人士称,这家投资机构目前员工数已经超过三百人,其中有近百人是为百丽单独招聘的经营人员。如果对照控股型PE的操作,这里有更大的差异凸现出来,投行人士唐军告诉我,通常控股型收购完成后,投资方需要对企业运营管理、财务状况、招聘等多个环节上介入,降低成本去提升财务指标,核心是精细化管理。但高瓴的做法却截然相反,先在自己的公司里招聘百来人做外脑。
张磊对百丽做精细化管理的说法是“我们根本做不到”。他年初在某家企业内部分享时谈到此事,用夸张的语气去称赞百丽管理层的效率能力比自己“好十倍”,并称在私有化完成后,整个公司的成本反而上升了,“我们不是削减成本的游戏,而是用创新提升份额的游戏”。
所以对张磊来说,投资进去之后,才意识到这是个把头部案例做成更大格局生意的机会,这当然是他乐于见到的。而百丽的另一层意义,则是给高瓴、给张磊充分展现了线下生意的迷人之处,或者说核心价值所在,那次分享中,在谈到高济医疗大手笔收购药房时,那也被他表述为同一套方法论向医药行业的拷贝。
就投资而言,行业研究也有两面性。那位接近高瓴的人士说,这家机构也曾在内部做过后台研究院,但很快发现“不work”,就把研究能力延伸到整个deal team上了。没问题先生说,高瓴有很大的二级市场资产在手上,因此他们在一级市场是利用二级市场的研究路径来布局的。可是否当真能够成竞争优势,却不好说。聂濂觉得,对于一级市场的投资来说,研究不是一个必须的“基础设施”,“研究做得好的人,投资不会太差,但投资做得好的人,未必研究很强”。
聂濂觉得,反而是百丽这种实操中觅得方法论,再向药房投资移植的逻辑,才是高瓴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包括更早启动的宠物医院投资也类似。高瓴2015年开始,便先后收购了芭比堂、宠颐生、安安、爱诺动物医院、宠福鑫动物医院、瑞鹏宠物医院等,到今年4月传出IPO消息时,高瓴已经在这块资产中囊括了1000多家诊所。
这种方法论上的竞争力,一方面来自独特的研究优势,另一方面也是长年累月交过学费的,聂濂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早年重注京东,就被证实了正确,但前两年在纷享销客上押注to C方式做to B生意则“凉了”,“所以,很多公司高瓴投进去的时候几十亿,怎么推到200亿~300亿?商业模式怎么做到这个级别?实际操作里,怎么通过钱的方式把它顶上去?最核心的能力,就要靠长期经验的积累。”
那位国有金融机构的人士单恕觉得,高瓴在研究上有着全方位的优势,他尤其看重干嘉伟、苏敬轼这些运营合伙人的作用,“通过这些顶尖的产业人士,才能做出标准的行业研究+运营增值打法”。单恕觉得,首先,对于大型投资机构,可以在“术”的层面做到极致。高瓴在《说明书》中称,自己是全亚洲在数据库上投入最多的基金之一,内部建立了基础数据研究团队与大数据分析团队,在线下/线上同步抓取并处理数据。此外单恕称,“只要他愿意,可以马上花几百万请麦肯锡打几千个电话,市场上任何研究工具都是标价的,只要花钱,你可以把时间节省到极致,百丽到底行不行?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电话打到一万个,或许就能看到你我没看到的东西。”
此外,研究也是一种壁垒更高的软实力。单恕先问我一个问题:给一个基层分析师足够的时间,可以把某项行业研究做到极致吗?没等我回答,他又立刻告诉我“不可能”。他说,行研的内核,是做好桌面研究之后,在“把人生大部分时间花在产业里”的企业家那里获取洞见。“顶尖的企业家关系,才能给你顶尖的insights。”
所以,高瓴为什么强调“我们是创业者,碰巧还是投资人”?为什么没问题先生会认为“高瓴的insights都来自张磊”?答案可能就在这了。
孤胆英雄式的焦虑

来源:IC photo
徐思季跟我说,去年在募资市场上,他所供职的母基金简直“(话语权)爆棚了”。
其实这家母基金原本口碑就不错,过往投资的人民币基金达到数百家,只是在市场上有掣肘,资金来源依赖地方政府,对投资地域限制很多。基金募资,就是个求平衡的工作,市面上的资金来源,除了这类国资背景的母基金,还有高净值个人,宜信、诺亚这类第三方平台,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以及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产业资本,那么为何偏偏是依赖国资的母基金成为角力中心了?
原因在于,上述渠道在去年悉数塌陷,徐思季不断在市面上收到诸如项目制基金份额乃至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的风声。这倒也并非小概率事件,而某些事件的连锁反应。去年资管新规发布后,一位人民币基金的募资负责人告诉我,直观感受是市场上的钱“断崖式”地被切断了,至今一年有余,余波也开始一层层地漾出来,高瓴和张磊身上发生的悄然变化,频繁走到台前来“多说话”的原因,也被其认为来源于此。
首先高瓴的人民币投资业务开启得相对晚。按照没问题先生的说法,高瓴虽然宣称管理着600亿美元基金,但其中绝大部分是美元币种。《说明书》显示,高瓴独立的人民币基金只有两期,一期的招募开始于2013年,规模43亿,而去年完成募集的二期基金目标规模原本为80亿,但close之后对外宣称为150亿元,大幅超募。也就是说,除了项目基金外,高瓴旗下独立的人民币基金大约不超过200亿元。
要处理跟人民币LP的关系真是不容易,张磊最近几次露面,都会强调投资节奏的重要性,在《说明书》里则不断向LP强调长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的理念,在这份70页文本文件中,“长期”作为定语用来修饰“价值投资”、“发展方向”、“竞争壁垒”等主语,重复了整整84遍。其实现实是,投得太粗放、太迅速不可取,投得太慢也有风险。黄仁立记得,早年柳青在高盛内部运作的那只人民币基金,问题就出在“慢”上,“几位认购1亿人民币份额的LP,拉着横幅跑去高盛办公室,刚刚两年啊,人民币基金七年呢,结果那只基金提前清盘了”。
所以投资节奏不能太慢,募资也不能停,那位基金募资人士说,对高瓴这种大体量的基金,挑战性更明显,“市场上真的没钱了。”投资市场就是这样,每隔几年,一个周期的浪头打过来,就让人们感叹年景太差。可徐思季坚信当下的“差”仍有些不同,他告诉我,据其测算,过往几年牛市下来,一级市场上存量的人民币资产至少五万亿,“2012、2013年就抢得很凶,好歹退了一波,但2014、2015年进去的时候,天使轮就要1个亿估值,我们遇到好几个项目PE快到100倍了,100倍在二级市场怎么退?不可能的。未来也回不了本儿,你觉得这个行业,还会有人投钱进来吗?”
“科创板呢?”
“5万亿资产,开个科创板能吸纳多少?”
在大的漩涡里,高瓴这艘大船在席卷中展现着不错的掌控能力。高瓴的美元基金向来宣称是长青(evergreen)基金(没有固定存续期限),而这在人民币市场上显然不可能实现。没问题先生告诉我,高瓴人民币基金存续期限是10+2的,时间还很充裕,这位募资人士分析说,因为高瓴的二期人民币基金是去年close的,因此很可能没有正面碰上资管新规。同时,品牌的口碑也在持续发挥作用,单恕所在的金融机构最近也在考虑投资股权基金,他们初步梳理了一份内部参考的基金名录,“说实话,我对张磊不太有感觉,因为他对外的信息全是‘摆拍’,我看不出此人的深浅,但我们一定会把高瓴放在参考名单上,因为投资一定是讲路径依赖的,LP没有任何动力去培养新基金。”
额度之外,另一层更高的挑战是募资方向。徐思季在市场上从来没有遇到过高瓴的人,“他们首选肯定不是国资背景的资金。如果说募资中的资金背景有链条的话,对高瓴来说,首选一定是保险、银行这些金融机构。”这一点他没估错,后来与没问题先生求证,得到的答案是,高瓴的两期人民币基金里至少有新华、泰康和社保几家保险资金。
那位募资人士告诉我,很多人民币基金都会在下半年启动募资,某家人寿下半年有一笔钱会出来投,很多基金都在盯着,而更多基金的合伙人都在此刻陷入传播焦虑,一种孤胆英雄式的焦虑,他们必须把个人顶到台前,化身卖方,供人品评,“真正募资的时候,就看你老板一个人,尤其对高瓴这种团队,LP就看张磊”。
他还带给我一个听来惨然的消息:一位早年同样被塑造为读书改变命运标杆的行业老前辈,前年在基金业协会处备案了一只30亿元基金的募资计划,直到今天,这条信息再未更新。
随后我在资讯平台上检索那位打过交道、为人和气的前辈的信息,却只能看到他在漩涡里愈陷愈深。
事情总是这样,有些人时代开启,有些人行将落幕,那些原本你以为始终会站在聚光灯下的名字,正是在不经意间隐匿、消失。端午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我做完这期选题最后一个采访,步行回杂志社,西二环已经堵成一片海,行驶在上面的金属机器们抖动着,漆面泛着夕阳的红色光晕,站在二环桥下,遥遥听着沉闷的发动机声,刺耳的鸣笛响,声浪与热浪浑然一体,席卷而来,这正像我在那位前辈身上目睹的巨大漩涡。
我想到张磊,想到那位前辈,想到在采访中与我周旋来去的每一位,如果说作为商人,行为讲究效率,又讲究落点,那么张磊和高瓴一定是怀抱着自觉意识来到当下、来到台前的。他正像是置身在大幕开启、半明半暗的魔幻时刻里,孤独又骄傲地,缓慢开启他的时代。